上世纪70年代,我曾经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翻译官。在震惊中外的9·13事件中,我曾和战友们一起写过血书,戏称为“血友”。这与“血友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实,“血友”之“血”,还可以泛指“血气方刚”之意。如此,“血友”就是“血气方刚之战友”的简称。每当一年一度的建军节来临之际,我都会沉湎于幸福的回忆中。今年的建军节即将来临,我想和大家分享文学翻译之外的我,其中包括一些军校翻译官光荣而特殊的工作和有趣的故事,以及一些当时创作的军旅诗。这些粗糙幼稚的文字虽然算不得好诗,但却是我那段闪光年华的真实写照。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4ZF$E[$1`V]PDIEE[5L(5K.jpg](0TemplateSongDL_clip_image001_0000.jpg)
1970年军政大学时期血气方刚的我
1
1968年我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根据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集体储备”的指示,全国所有外语专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正式分配工作之前,统一被安排到军垦农场,带薪接受再教育两年。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俄语专业毕业生则被安置在天津南郊解放军某部农场,一边种水稻,一边接受再教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应届毕业生与我们混合组成一个男生连。
全体学生按部队编制,货真价实的军事化,住的是简陋的稻草屋,睡的是连排的土坯炕。全连三个排,十二个班,每排四个班。每班十二个人,设正副班长,由学生担任。排长一人,由解放军担任。除去十二个班之外,连里自然还有一个炊事班。炊事班由司务长挂帅,炊事班长是解放军。我在第二排,第七班。排长郝增柱,河北人,看起来大大咧咧,实际上非常细心,不仅热诚可亲,而且口才不错,能力特强。连长宋连奎,山西人,心地善良,胸无城府,文化水平不高,说话直来直去,和他在一起觉得无拘无束。指导员周玉坤,湖北孝感人,明眸皓齿,两腮红晕,看上去颇似文弱书生,但却年轻老成,弱中带刚,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只是表情稍显严肃,有些令人生畏,且湖北口音浓重,听他说话似乎比听英语还难!
每天六点起床,然后晨练跑操,继而以排为单位,列队由郝排长训话,这叫“早点名”,包括点评各班表现,布置当天任务等。之后刷牙洗脸,吃早饭,再之后就开始一天的主要任务,一边种水稻,一边改造思想。一天到晚,各项活动安排紧紧密密,严严实实,针插不进,水泼不透,但就是没有将一分一秒分派给英语学习。
在农场的两年时间里,种过两季水稻。从冬天的农田水利建设,也就是挖水沟,到来年平田整地,育苗插秧,再到农田管理,诸如灌水排水,施肥锄草,乃至秋收冬藏,这一整套流水作业的每一个环节,样样不少。两年下来,标准的一介农夫!
2
不过在农场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接受解放军再教育而不是种水稻,种水稻是为了改造思想。
我自幼生长在农村,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这似乎是天性。1957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学校搞勤工俭学,就曾经种过水稻。1958年“大跃进”年代,学校停课,我和同学们一起到处参加农业劳动。我虽然是北方人,但种水稻的活儿并不陌生。我尤其喜欢和擅长插秧,速度之快就连一般的南方人也追不上。我从小就给家里的小毛驴打草,使用镰刀的技术炉火纯青,因此在割水稻时,我总是摇摇领先。从田里往打谷场背稻捆,我也显示出超乎一般的力气,这大概是因为小时候给毛驴割草自己背回家的缘故。所以,我虽然看似瘦弱,背起稻捆却没有觉得很累,而一些身材比我高大很多的同学,却时常累得呲牙咧嘴,气喘吁吁,真的比不过我。我在劳动方面的确有不错的表现。
3
大约在1969年春季前后,北京市曾经掀起清查“文革”中“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展那次运动的原因,是“文革”期间北京有个“五·一六”组织,他们搞过旨在打倒周恩来的“倒谢”活动。“倒谢”就是打倒当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主任谢富治。据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里也有人参加,因此要在农场开展清查活动。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很快就在全连展开了。自我感觉在“文革”中曾经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或排错过队的人,个个人心惶惶。一时间,原本风平浪静的农场,旋即阴云密布,一场政治风暴旋即来到。随着专案组的成立,被查学生立即赶写材料,交代问题。态度不老实的还在会上遭批判,严重的甚至被关禁闭。
我们南开大学的学生其实只是“陪绑”,除个别在“文革”中的活跃人物之外,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触及到。清查工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但是在夏秋之际,也就是在连里抓反革命学生的关键时刻,突然传来分配工作的消息。
4
分配工作,不啻石破惊天!这是学生的大事,就连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也不得不让路,因此运动紧急灭火,全连上下总动员,火速转入分配工作。没有问题的人心花怒放,有问题的人忧心忡忡。因为运动草草收兵,他们那些尚未结案的资料只能往档案袋里一塞了事。试想哪个单位敢接收这样的人!于是他们就沦为分配工作的“处理品”。
分配工作十分强调阶级出身,不要说本人出身不好,就是女朋友出身不好,都要受到影响。我们班有个男生,本来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据说起初分配他进入公安部门。但因为他的女朋友是资本家出身,连里领导就让他做出选择:要工作,就不要女友;要女友,就不要工作。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女友,放弃了那份令人艳羡的工作。这样的选择在当下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却被视为不服从国家分配,因此备受诟病。
相比之下,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如愿以偿地圆了参军梦和翻译梦,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当了一名翻译官。
圆了参军和翻译梦,好心情没得说。但经过这么多年,静下心来想一想,当初的确不应该盲目乐观,因为在遥远的大学一、二年级学的那点儿英语,被搁置四、五年之后,已经所剩无几,这为日后的发展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先天不足。带着这种先天不足,我还有本钱去担当翻译这一神圣职责吗?书到用时方恨少,以我日后的切身体验,这的确是千真万确至理名言,因为每当翻译出现难题时,这种先天不足就出来掣肘。
不过,遇事先说三分好吧。此一时,彼一时,突然之间就当上了军事翻译官,这毕竟是一件美好的事,而我的翻译人生也毕竟从此拉开序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是中国最高军事院校发展的一个建校阶段,1969年2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撤销,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的筹建工作开始列入议事日程上来。1970年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最初成立了若干大队,后来改设军事、政治、后勤等系。教学内容以突出政治为中心。首任校长黄永胜,政委张秀川。 1971年“9.13”事件后,学校进行了整顿。此后校长与政委分别是肖克和唐亮。 1972年8月起从部队召回并选调了一批军事教员,恢复了军事课的教学内容, 1975年开办了军事班、政治班、师以上干部读书班、抗登陆研究班等。 1977年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的基础上,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建制被取消。1985年12月由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又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我入伍的时候,军政大学还没有“系”之说,只下设相当于“系”的五个大队,前四个大队在位于颐和园后面红山口的总部,第五大队在昌平县原来的一所军事学校旧址。军政大学是军级单位,五个大队都是师级单位,因此别看人数不多,大队长都是师级干部。学院以前四个大队为主,第五大队为辅。前四个大队是内训,学员都是团以上干部,采取轮训形式,每期四个月。我所在的第五大队是外训。
所谓外训就是训练外国军事学员。这些学员不少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访华团成员,有的就是一些国家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有的甚至就是居无定所的游击队。除此之外,偶尔也会接待一些外国驻华使馆的武官等。
入伍后当上了翻译官,但第一项任务却不是搞翻译,而是随着大队政委住进了军政大学在北京红山口本部的刘伯承元帅曾经的帅府。那是一座漂亮的小别墅,建在一座小山顶上,那里是全校的制高点。我的任务是帮助陈政委整理哲学讲稿。
昨天还住在农场简陋的土坯房里,今天就住进了豪华的帅府,昨天还在一边种水稻一边写自己改造思想的材料,今天却是帮助高级军官整理外训讲稿,真是一个在山脚,一个在山巅,差距之大令我简直喜不胜喜,狂不胜狂。
当时的学员很多都来自阿拉伯地区,因此阿拉伯语翻译任务很多。而英语翻译的任务非常少,我一共才参加过两三次教学任务。第一次是接待坦桑尼亚驻华使馆武官辛巴少尉。这一期的学员只有他一位。学习内容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
五大队本部在北京以北的昌平县城,此外,在北京东南的通县县城也设立一个教学点。为坦桑尼亚驻华武官辛巴少尉授课的课堂就是他在那里下榻的客房。由于学员只有一位,而且级别较高,因此上课方式规格也高,采取一对一的小灶式授课法,除了学员和教官之外,翻译官就是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为了照顾辛巴少尉的生活,我就住在他隔壁的房间。每日耳鬓厮磨的也就是我们三员:学员、教员和译员。
平生第一次以翻译身份零距离接触外国人,心情格外兴奋,因为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我的翻译舞台从此便拉开大幕。数月的任务顺利完成,感到收获颇丰,成就感颇强。
6
随后又接待了一个有十八名学员的赞比亚军事代表团。由于学员多,采取的是教大课方式。这期学员的级别较低,大多是部队基层士官,带队的是一位中校。培训内容仍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除理论课,还有实践课,就是野外操练和武器操作。
野外操练从单兵战术到营团级山地作战的战略战术,逐一进行。具体内容从最基本的列队训练开始,也就立正稍息、左右看齐、左右转、齐步走等,然后再进行班组、连排、营团作战指挥等。
武器操作课最新鲜,不过喜文不喜武的我并不喜欢,虽然如此,什么长枪短炮也跟着学员一起摸过了。手枪、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高射机枪、迫击炮。这些武器,不仅要教授性能、用途,参加实弹射击训练,有的还要教授学员会拆会装。
这一期的课程分两处进行。前期在昌平县的五大队本部开展,如伏击战、夜袭敌炮楼等课目就在附近十三陵水库一带的丘陵间进行的。后期是在南京某部队开展的。除了在附近山地开展磨爬滚打的单兵战术训练之外,还增设了较大规模的营团级作战指挥。翻译不仅是别人的嘴,还是别人的腿。作为翻译的我,必须和官兵形影不离,照样要和他们一起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不仅要拼英语,还要拚体力。若果教官和学员抵达山顶,而翻译却没能跟上,这等于双方都没有带嘴。这期下来,感到收获更大,喜悦之情难以言说。
昨天还是再教育对象,一夜之间华丽转身,变成教育别人的人!此外,令时人艳羡的草绿色军装,红艳艳的领章帽徽,如今都穿戴在我的身上。从前同学之间直呼姓名,而现在却是翻译官长翻译官短,美称不绝于耳。更有甚者,出入大门时门卫还要给我立正敬礼!所有这些,从前做梦都是想不到的,因此整日里心花怒放。
7
但是事情总是在变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尤其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变化,军政大学的外训任务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据说从前在部队进行的外训任务被转交给地方部门,学员到井冈山和延安等革命圣地边访问边学习。这样一来,军政大学的外训任务就逐渐稀少起来,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外训任务更是少而又少。
长期没有外训任务也不能闲着,学院要组织政治学习班。一进入学习班,就领到学院自己印制的欧洲古典哲学以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由教官讲述,然后讨论。讨论的内容涉及各流派的哲学思想,最经典的当然莫过于耳熟能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学习班的学员大多是教官,不少都是“文革”前政治学院的教官,名副其实的科班出身,因此个个侃侃而谈,口沫横飞!我这个新兵当然只能洗耳恭听,无缘置喙。其中令我记忆犹新的就是英国貝克萊大主教的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理论,说是物质的存在由人的感觉而决定,比如一块石头碰了你的脚,它就是存在的,如果没有碰到,就是不存在的。还有比如一只杯子,它本不是什么具体的物体,只是人们所感觉到的颜色和形状的组合。甚至还讨论过杯子被打是否会有疼痛感觉之类有趣的怪问题。
所有这些都与本职工作翻译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听多了难免倒胃口。尤其是刚刚离开广阔的稻田,现在一下子被关在逼仄的教室里,一坐就是大半天,加之不少人香烟不离口,喷云吐雾,在这样云雾缭绕的环境里真是如坐针毡。
好在学习班所在的别墅楼外就是学院自己的一片桃园。如果赶上春季,上午10点的课间休息一到,我们几个新兵就像出笼的小鸟,立即跑到桃园里去观赏美丽的桃花,谈天说地,早把那些味同嚼蜡的哲学概念忘到了脑后。如此说来,那也算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终生难忘。
8
新入伍的大学毕业生必须下连当兵,这是军事铁律,我当然也不例外。1971年8月初,趁外训处于淡季,我在黄大队长亲自陪同之下,乘坐他专用的黑色吉姆轿车,前往河北省保定市地区的松林店,到某军的一个野战部队下连当兵。就从陪同人员来看,其重要性便可略见一斑。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到连队我就碰巧赶上千载难逢的全军首次摩托化拉练,大家都说我很幸运。其实幸运不幸运,这个时候怎么能如此肯定呢?面临光荣的任务,全连官兵意气风发,为这次远程摩托化拉练紧张有序地做着准备。我成天和那些干吃辣椒如吃荔枝的湖南兵一起磨爬滚打。从操练步伐,到持枪列队,从单兵战术,到班组,乃至大兵团作战,在加上真枪实弹的射击训练,简直无所不包。不久部队就正式出发了。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终于抵达目的地辽宁省赤峰市郊外的丘陵地带。
在一个小山村安营扎寨之后,部队就开始野外训练。第一个科目就是在山坡上挖猫耳洞。专业术语叫掩体,大白话叫藏身洞。但猫耳洞还没挖好形势就突然生变。也就是抵达那里两三天之后的一天下午,太阳刚刚偏西,大家正挖得起劲,突然一声刺耳的哨声打乱了大家平和的心绪。一听那又急又响的哨声,大家都下意识地站起身,只见首长们匆匆赶来,一脸的严肃,召集大家立即回营地待命。出了什么事会如此突然?当时谁也不敢问。回到营地后,连长命令大家立即打背包紧急出发。
9
长龙一般的车队很开就出发了。虽然大家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并不糊涂,部队没有继续向北开,而是千真万确地往回开。经过日夜兼程,部队很快进入战略要塞河北省的古北口。但是再继续前行的路程并非回营房,而是在昌平县城向北一折,开进另一战略要塞南口镇。车队继续前行,一直向大山深处进发。部队最后到达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居庸关才驻扎下来。
部队驻扎在山坡的一个林场里。首要的任务是就地待命,在山坡上挖猫耳洞。约莫两天后,形势逐渐紧张起来,人们都在揣测出了大事。果不其然,一天上午连长终于召开全连大会,吐露真情。说是外面发生了情况。至于什么情况,他仍然守口如瓶。他究竟是故意卖关子不愿说,还是有命令不能说,这在当时是不得而知的。不过他的一席话却使每一个人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他严肃地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大家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让你开枪打谁,你就打谁,别的你就不用问。不管是工人也好,农民也罢,即便是当兵的,打起来也丝毫不能心慈手软。还说部队的政策是内紧外松。对老百姓什么也不讲,而部队内部却要作好一级战斗准备。最后他还说,别看现在是蓝天白云,说不定转眼就是炮火连天。
随着形势的明朗化,战斗气氛越来越浓。从那次会议起,人人都要和衣而睡。除了原来带在身上的真枪实弹外,现在每人又发了三颗手榴弹,而且要求随时别在腰间。从那以后,三天一表态,两天一宣誓。不仅用嘴表示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而且还要写血书。有人用牙齿咬破中指在纸上写:誓死保卫毛主席!有人用刀划破食指在白布上写: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我是下连当兵锻炼的,这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刻,在这关键时刻,我怎能落后呢?于是我有样学样,也划破手指,在白布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血淋淋的七个大字:誓死捍卫毛主席!
可是说来奇怪,忠心也表了,血书也写了,就是不见敌人的动静。岂不是白白浪费大家的感情和鲜血?事情有时就是这样不如意,你想着敌人来,他就听你的话吗?大家今日盼明日盼,盼蓝了眼睛,等着战场立功,可这敌人就是不作美。等到后来,终于还是没有露面。就这样部队在长城脚下的居庸关白白耗了一个星期左右,才接到命令打道回府。
撤军还不彻底撤。出了南口,往东一拐,开到十三陵水库以南的一所军事院校旧址驻
扎下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所院校旧址就是和我所在的军政大学外训队一墙之隔的邻居。拉练拉练,竟然把我拉回了老家!领导一看,干脆就让我离开某军返回军政大学,郑重其事的下连当兵也就这样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10
我带着一头雾水,回到学院。起初还是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跟着别人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军队里传达上级文件是要严格按照级别办事的,我们这些新入伍的一开始还轮不到听。不过从那些听过文件的人言谈话语中,还是逐渐能品出点味道来。尤其当我看到他们悄悄地把林彪语录从墙上撤走时,一切似乎都已明了。当然,听过文件的人大都不敢把这层薄薄的窗户纸捅破。不过毕竟有一些心里盛不住事的人,暗自透露林彪出事了。只是不敢细说。而就是在这“雾里看花”的情况下,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
虽然中国出了大事,军政大学的外训仍在继续进行。当时,接待了一批非洲军事代表团,安排给他们讲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配合教课,还从连队请了一位毛泽东著作学习积极分子现身说法。那名战士当然不知道林彪出事,因此讲稿中仍在引用林彪语录。奇怪的是,他的讲稿事先也未经检查。听到战士仍然是满口的林副主席,不时地引用林彪语录,在座的首长如坐针毡。一个个口将言而嗫嚅,不停地向我使眼色,示意不让我翻译。这个时候,他们好似忘了我这名新兵还没有资格轮到听文件。
不过我当时的革命责任心还很强,再加上心里早有那些小道消息垫底,当然应付自如。我当时真好像连升三级,自作主张地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没有翻译战士引用的林彪语录。只是根据那段语录的时间,随意用一些别的话搪塞过去。说来真是好笑,本来生性木讷的我,居然能一下子巧舌如簧,中外双方都没有听出破绽!下课之后,外国人一走,大家就急忙凑到我跟前,问我是否翻译了林彪语录。我把实情向他们一讲,他们才长舒一口大气。好像天终于没有塌下来。而我真的好像由五尺男儿变成了补天的女娲!其实呢,即便我翻译了林彪的语录,天就会塌下来,地球就会不转吗?想一想,那时的人真是颟顸透顶!
这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过去之后,又等了一些日子,中央的红头文件才公开向普通军人传达。林彪死亡的消息才正式大白于天下。我在惊愕之余,仔细回想拉练的前前后后。尤其是从赤峰撤回到北京以北的居庸关,正好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之后的一两天之内。后来又经过证实,我们之所以紧急停止拉练,转移到居庸关一带,完全是因为林彪事件。再后来大家都说那就是利用某军这支精锐部队保卫北京,以防天下大乱。到这时,我才如梦方醒,同时也感到万幸。如果真的打起来,我这名枪打不准,手榴弹投不远的书生,必死无疑。
—节选自我的翻译自传《译心》
附诗一组:
1. 夜间平田
夜半荷锄归,
冷风习习吹。
浑身沾泥水,
惬意入心扉。
(1969年5月16日天津南郊部队农场)
2. 雨后
五月多喜雨,
满田已发青。
日夜忙不休,
换得好收成。
(1969年天津南郊)
3. 春湖
平湖烟雨欣欣落,
远近沙汀绿茸茸。
泽边有人歌不已,
春在心花别样红。
(1970年春天津南郊)
4. 稻田放水
明月高高照清泉,
谈笑风生下秧田。
凉风入骨方知爽,
夜露沾衣不觉寒。
喜勘秋谷多如海,
苦思汗水状如澜。
情击沸海连云汉,
稻花香里唱丰年。
(1970年夏天津南郊)
5. 小憩
溪头野花里,
赤脚坐相谈。
汩汩清渠水,
朗朗二心间。
(1970年夏天津南郊)
6. 慰友诗
- 好友虞和富因母病故久久未归
其一
悲心切切日夜浮,
遥恐兄弟哀得殊。
寄意流星过扬子,
何时海滩共学书?
其二
常借观图妥梦乡,
眈眈所向唯溧阳。
莫道千里迢迢远,
思绪乘风早过江。
(1970年4月天津南郊)
7. 隔湖听钢琴协奏曲《黄河》
泱泱大河曲,
滚滚天上来。
思风发胸臆,
哮然湖自开。
(1970年春天津南郊部队农场)
8. 别坦桑尼亚驻华使馆武官辛巴少校
今别一壕之战友,
峥嵘岁月漫重游。
松间月下听故事,
亭前雪后植谊柳。
大城泽畔同练武,
小楼灯底共学书。
迢迢两地隔远水,
可见虹桥跨海出。
(1971年夏北京通县军政大学)
9. 读家书
拆开信儿心不安,
胸中即刻卷巨澜。
别人家书贵如金,
我的家书重于山。
莫似他人钱如水,
我的分文抵万贯。
我的家书如警钟,
常敲常鸣好无边。
教我艰苦而朴素,
不要忘本颜色鲜。
须当努力奔事业,
不得浮生半日闲。
(1971年10月17日北京昌平军政大学)
10. 桃园剪花
春山生紫雾,
修枝剪花忙。
鸟嬉争乱语,
蕊醉沁幽香。
落英红雨下,
笑浪轻雷扬。
七月蟠桃美,
先与谁人尝?
(1972年春北京昌平军政大学)
11. 野炊
秋雨绵如丝,
山风凉且湿。
野灶烧难旺,
行军不堪迟。
到时看米饭,
粒粒白心子。
炊者心惭怍,
食者乐不支。
此饭吃长劲,
冲锋苦不辞。
(1972年秋下连当兵河北省拉练行军途中)
12. 夜行军
山飞月追,
隐隐现现。
风吹水回,
涟涟漫漫。
我行在山后,
我行在山前。
我行在山下,
我行在山巅。
山路何盘盘,
首尾接天。
车灯何灿灿,
光弥河汉。
不雨何雷,
车轮飞转。
不云何龙,
车队萦环。
凌厉越万水,
逶迤跨千山。
我行穿滦水,
我行越燕山。
我行复天上,
我行复人间。
(1972年8月 记河北保定松林店
至内蒙古赤峰拉练途中)
13. 宿营
月上燕山脊,
露宿滦河西。
草软充衾被,
天高做幕帷。
因风听蟋蟀,
入梦杀声急。
人醒山犹睡,
方觉露沾衣。
(1972年8月拉练途中)
14. 承德瓶子山
烟峰雾树,
神瓶突兀。
千载悠悠,
凿天接露。
仙露酿酒,
流香飘馥。
千杯万斛,
敬献风流。
(1972年8月拉练途中)
15. 香山行
忽觉应惜凉秋晚,
度病偷闲到香山。
哪来和风拂人面,
处处霜叶红欲燃?
(1972年秋北京红山口军政大学校部医院)
16. 与XX国友人交谈
海内行云客,
天涯友心连。
倾山倒海志,
莫逆语绵绵。
(1972年)
17. 陪同外国朋友游十三陵
燕山脚下十三陵,
多少血汗修造成。
不知盛气今何在,
空留古墓各西东。
今代英雄一挥手,
新辟良田无数有。
当年禁土成乐土,
一任远近宾客游。
(1972年)
18. 夜练
- 与坦桑尼亚学员练夜袭炮楼
夜静天如墨,
发兵敌堡东。
两路西沟上,
两路由北攻。
一队刺岗哨,
一队打先锋。
攀石须仔细,
拨枝要轻盈。
敌哨斜枪困,
我军挥刀猛。
不见还击者,
但闻喊杀声。
顿时敌营乱,
不无求饶命。
手雷连天震,
龟壳划为坑。
历时三五分,
迅速合聚拢。
一路哈哈笑,
归来乐融融。
今日多流汗,
来年建奇功。
(1972年北京昌平军政大学)
19. 南京长江大桥
一江一条龙,
一桥一弯虹。
苍龙饮沧海,
长虹锁长空。
桥堡铸天外,
江墩踞龙宫。
就夜观灯火,
直是银河明。
仰视天成矮,
伸手可扪星。
俯视水渺远,
疑在天街行。
挽来千百险,
化作一桥雄。
真从云中坠,
非打地下成。
遥望大环宇,
深邃永无穷。
(1972年于南京军营)
20. 赠友诗
其一
正月十五冬已尽,
岭上寒气犹袭人。
别看大山仍披雪,
细草初黄也是春。
其二
归心如火般般暖,
忘却棉衣能祛寒。
谁知一夜北风起,
咳到如今还未痊。
其三
蛛丝小路密麻麻,
不知哪条到天涯。
站在山顶朝下看,
顿觉条条清如画。
(1972年北京昌平军政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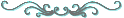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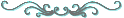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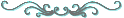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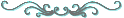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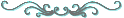
 走进美丽的南开园 走进美丽的南开园


【附】敬请大家一起呼吁:祖国文明建设应从央视和国营媒体禁刊酒类广告做起。酒,从精神到肉体已经伤害了无数国人!
-《海外南开人网》敬启
|



